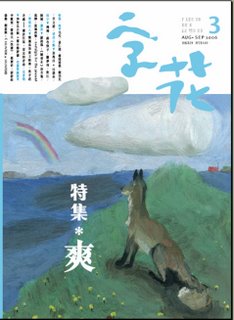和人大吵的時候,對方說「道歉對你而言是沒有意義的」,我心想你小子怎麼知道,我和你可沒那麼熟。後來我找到了這段書鈔:
然而,「抱歉」是多麼詭異而歧異的一個語彙,所有的抱歉之語(對不起、我錯了、失禮、請見諒之類)都不能免除這個抱歉者「已然」或「既然」的一個強硬立場;抱歉是一個迫使抱歉對象接受已然或既然如此之事實的字——事實容或是發生之中或發生之後,則抱歉這個語彙正暴露了它的無效性,也惟其在理解了抱歉的無效性之後,我們才能重回apology這個字的雄辯淵源,它的意思是辯護。其實,它的意思是辯護。 視文學為「苦悶的象徵」、「人生的投影」、「苦難的救贖」者,恐怕無從體會:文學工作祇是它自己的辯護,而這辯護之所從來,乃是由於文學(詩)無法和人(人所以為的)它所映照的廣袤現實逐一對應。相較於正義、公理、世事、時局,哪怕是相較於天氣和愛情,文學或詩之單薄脆弱似乎不言自明——它祇能鮮活生動地顯現在紙上。 ——張大春:〈迷路的詩.序〉(楊照:《迷路的詩》)
於是我在這個意義上喜歡張大春——儘管他多麼滑頭,但在某些關節,他知之甚詳。有機心的人的誠懇,就是承認道歉的不可能——這種誠懇還有一類膺品,就是聲稱明知無效而樂得清閒。真實不能停止膺偽的衍蔓,我不能停止自己辨認。
鈔下這段書時是2000年,我還在使用 s976274@cuhk.edu.hk的電郵。這段文字裡有其對應於「懺悔錄」和「歷史」的脈絡,初讀那時更無意指責文學無法對應現實——但我畢竟還是留意到了「無法對應」。而自那時開始,在人際關係層面上的看不開,算是達到了一定高度。
***
是的,自此之後我接近完全不信任道歉,大部分直抒胸臆的書面剖白亦打個七五折,寫給我的詩殃連打折。開始寫作以來,就和太多寫得太好的人周旋,結果我誰都不相信。喜歡寫情詩的人大概不忍說破(像鴻鴻的〈情詩為自己而作〉說得多麼清淡高遠),就讓我用一種商賈的語氣來說吧:我這樣辨認某人的情詩能否竄紅:那些詩會否「被認錯」。即會否被對象以外的其他人認錯,誤以為是寫給自己的。錯得愈厲害,證明情詩質感愈強,將愈受歡迎。
這就是「無法對應」的力量。
所以我不寫,也寫不來。與某些前所未見地具有突破性的詩相比,我寧願相信別人在公開場合一發不可收拾地抄著的《戀人絮語》。尤其因為我不喜歡《戀人絮語》。
***
軟硬演唱會,賣的當然是記憶。全場人為整蠱電話而會心大笑,並沒有怎麼聽過軟硬的我感到他們所覺得的溫暖。葛民輝很擅長學習無聊的細節,他假扮之維肖維妙在於連那些停頓和猶豫和重複都像真的一樣——這些領悟都已過時了罷,被無數人領悟了無數次了吧。演唱會算是好看,但我始終感到某種不對位——軟硬自嘲地問「難道大家進來只想聽我們重新做一次整蠱電話?……」我懷疑,是的。
這是一個大賣「集體記憶」的場合,但我懷疑軟硬所擅長的或者不是回憶——他們始終善於捕捉商業運作裡的某些必要之惡,然後放大、反諷,撫平參與者的不自然,召喚某種「搵飯食姐」的包容,某種在心知肚明的前設下,毫不費力只需一點聰明的幽默。我和詩詠就是這樣接受了手上那對「fantastic!」——當然還有手機螢火蟲,電子機械重設童年的夢幻、浪漫象徵——我因此深信軟硬(或起碼林海峰)強項,是那種「明日話今天」的帶領性,而非追溯回憶。林海峰講軟硬結識過程,如何從明愛白英奇到商台,日夕相對到拆夥分道——中間明明是有一道不可言說的斷裂,引發無窮詮釋的斷裂,怎麼也不能輕描淡寫地訴諸「太忙,沒溝通」就掩埋過去的。記憶無論如何都涉及敘事,而追求圓順的敘事只會放大裂痕,就算林海峰如何靚仔,在這個環節他沒有幹得漂亮。我只能揣想,那種中午放lunch衝上其中一人家裡煮麵的方式會令「同黨」之感如何強烈,那種每天清晨一起搭的士番工、一人截車一人備早餐的習慣,又是怎樣在無所謂的情況下崩潰的。
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忘記那個晚上。甫開場,就是主題曲Long Time No See,當然是「全場人嚟大嗌聲好久不見」那種。我敲著手上的「fantastic!」,Long Time No See四個字隨著滿場「fantastic!」的運動以嘈雜人聲的形態齊整爆炸,我知道了將來會發生的事。啦啦啦啦啦啦 全場人嚟大嗌聲啦啦啦 湖互惡烏污惡 我嗌你啦啦啦啦 你有冇聽見。這麼多陌生的人憑藉無意義的句子衝入你的核心,代人講對白上了身一樣。整首歌變得無限辛酸。我對好久不見這種主題無可無不可,但我只是來聽演唱會的,沒準備好遇到啟示和預兆。那天是八月二日星期三,三號風球,沒有毀滅任何東西。
回頭再說,「捍衛地球」,這種姿態才是真正的進可攻退可守,說出來又口響,沒人拿你當真,詮釋一下說不定還算做到了,真係做到更是超勁,贏晒。長期與善於使用語言但不能兌現承諾的人相處,在離身一點的時候我會能夠欣賞「大話」的完美策略位置。我覺得軟硬演唱會的真正弱點在於,就算把捍衛地球幽默地接受,我還是感受到台上二人不知將來怎辦好的不踏實感覺。他們還未想到要幹些什麼,只設計了一個「捍衛地球」的聰明口號。That’s fine, as artists.
***
七月三日論文口試。七月二日晚突然大崩潰。溺水一樣打字上msn:「崩漬了」。對方見連字都打錯,知道大鑊。我都不知我們說過什麼,總之哭累了就睡覺去,口試講稿亦沒準備好,一如論文的後半部分,期期艾艾蒙混過去。
其實那晚是聽了黃耀明〈身外情〉。我並不特別喜歡這首歌。它麻煩的地方在於,它是我其中一個拒絕了的世界,柔軟、清澈、遙遠、豁然開朗、留有餘地。「雲過天清,忘掉我們曾盡興」,全都錯了。沒有雲過沒有天清,沒有盡興沒有我們。問題在於,有沒有忘掉呢?「忘掉」是及物動詞,沒有後面的賓語的話,它是不能成立的。另一方面,「沒有忘掉」,是怎麼回事。
這是一個怎麼回答都錯的問題。
***
我後來所仔細思考的是,在獨居的隔音的屋子裡,為什麼要乾嚎呢?然而重複發生之後我終於明白,那是身體的決斷:它喜歡抽搐與痙攣,扯動氣管連接的心肺,喜歡呼吸困難。唔到我話事。
我始終堅持,在我所拒絕的許多世界中,〈身外情〉的世界並沒有什麼額外特別的。並不是我與之特別接近、拒絕特別困難,才會有上述的「身外情效應:身體的決斷」。然而,對獨特性的否認背後,涵蘊了界限的模糊——即可以在任何毫不相干的情況下,引發抵達核心才會有的崩潰、實在界的漂浮。如果我堅持現時,並沒有對我所居住的世界的適切表述,那事情就更怪了:與一般代表著才能的獨特聯繫方式不同,我的聯繫全都是錯的,而我的身體就在錯誤裡自行決斷。無法排除任何錯誤。
當然,這種無限美好的,失控地錯誤的神遇,我只到達過幾次。
***
七月和葉寶琳去求寶蓮寺觀音靈簽(詳情另記)。其中一枝是這樣的:
第二十簽 中簽 姜太公遇文王
當春久雨喜開晴。玉兔金烏漸漸明。
舊事消散新事遂。看看一跳過龍門。
好到自己都嚇一跳(咁都中簽?)。事實上那次求的一大堆簽,都是好到我們兩個都嚇一跳。葉寶琳簽的主題是「守舊」,我的簽則在在暗示要「前事不計」。嗯嗯,如果他日我眉飛色舞黃袍加身,必定是因為我前事不計了。因此,在美好的未來到來之前,在那些門縫後的光照到我面上讓我涕泗縱橫之前,我已知道了。
但我不要。無論如何痛苦,我還是要留在那個換算等值的世界,指認未曾勾銷的前事。就算我所有的計算都是徒勞並無可告語的,就算我所有的計算都是錯亂而且虛構的,並因此而背離人生所有的好運,我都不要。
 畢業的歌
畢業的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