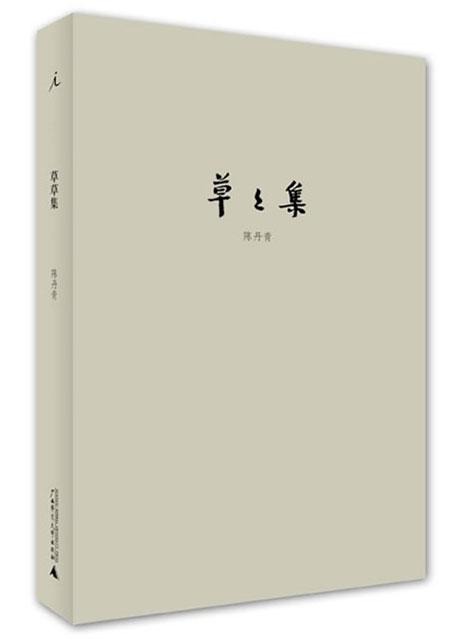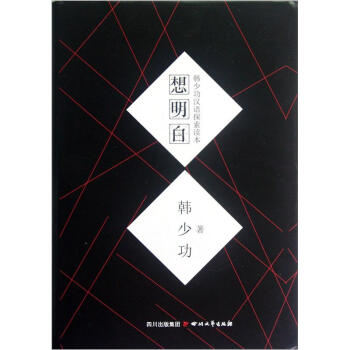親愛的,等你讀到這篇文章時,我已經身在愛荷華了。或者我在jet lag中五里霧中,但陷入迷霧之前我的留言仍是,相信距離乃是要讓我們發現不可割離的親密。
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,因為白先勇與聶華苓而著名,香港作家早如戴天也有去過。近年如董啟章、韓麗珠、謝曉虹等的前赴,彷彿都好像在他們寫作生命中負載了點點意義。我最羨慕還是陳智德,他在愛荷華那裡偷得一點時間,寫出了《地文誌》這本對香港而言頗有意義的好書。香港作家缺乏結構上的楷梯或突破點,也在現實上欠缺創作的時間和空間。所以何鴻毅家族基金近年支持香港作家到愛荷華交流,有類近於荒漠甘泉的意義。
作為一個出版不算多的近中年作家,必須感謝推選者的厚愛,讓我有機會在七頭奔馬的生活裡抽身,好好思考寫作。尤其KF先生,他在幾年前就已推動過我,惟我總是忙亂,辜負他的好意,直至今年。我常常把文學工作放前,把自己創作的事放後,難得總是有他人記得我該好好寫作,不要浪費。像黃碧雲,那麼苛刻尖銳,看過《若無其事》及《眾音的反面》之後,都給我暖熱誠實的回應。游靜一邊說明美國的帝國心態,一邊關心我實際生活和寫作的事。其餘朋友如謝、韓、郭、良、閃等,還有臉書上相熟不相熟的朋友,都既實際又抽象地給我正能量。無以為報,唯有再勉勵自己要以寫作來負起對世間的責任。在此感謝我的譯者徐晞文小姐,以及2000年中大《譯叢》選譯敝詩〈定住〉,讓我的作品有英譯可以向外交流。
心裡記掛文學館的各項工作,惋惜錯過蕭紅《黃金時代》公映的盛事。更掛心處於關鍵時刻的香港,各位抱持理想的朋友們。香港人總是被置於他人所設的框架之下掙扎徘徊,香港讓我最感動的,總是它「不認命」的時候。
在政治低氣壓、極權氣氛接近的時候,我愈發相信文藝和連結的重要性。所謂極權統治的意思,就是政權的權力痕跡盤據外在的所有場所與公共空間,明火執杖;而無權無勢信念正確的個人則形孤立。相對於極權的格式化,文藝肯定每個人的殊異;並且,它可以用非功利的興趣形式,讓我們連結。蘇俄東歐,都曾有很多文藝小組織,靜靜保衛著人的內心與行動的能力。像辛波絲卡〈對色情文學的看法〉一詩,以幽默的反諷,反抗極權統治對於文藝的誇張、污名化及監控。極權會將文學聚會說成「幽會」,但辛波絲卡說「他們幽會時唯一濕熱的是茶水」,我們在發笑的同時,就些微捍衛了自己自由的內心。在極權的世界裡,我們要比以往更珍惜文藝,相信自己本來就擅長與熱愛的事物。
歐陽江河有一首詩,叫〈成都的雨,到了威尼斯還在下〉,他說他把成都隨時帶在身上,成都和威尼斯並不像地圖上那麼遙遠,而只是詩句裡相鄰的兩個詞而已。親愛的,請加油,讓我們在文字與句子中,閃耀如珍珠,照亮現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