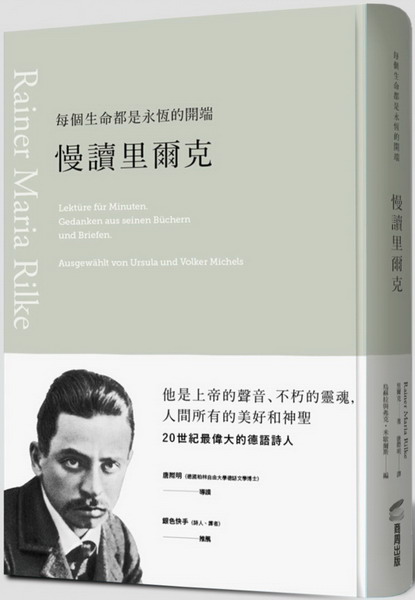愛情本來不是我的課題。然而我們誰又能逃得過愛情?張愛玲說:「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,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,後看見海;先讀到愛情小說,後知道愛;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,借助於人為的戲劇,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。」此所以我們知道愛情小說何以會大賣:它始終是人類的一個免不了的需要,可以在書中經歷未經歷過的,讀過也就是經歷過了,把那些傷痕帶在身上——而現實可能是相反的,宅女、毒女、剩女,讀過書便擁有了那些愛情故事。
時移世易,據說六十後放縱任情,七十後對愛情無幻想,八十後愛情是多元關係,九十後覺得愛情很麻煩。愛情是否也會褪流行?以下的書單,或可名為「獨身女子是如何煉成的」。
當愛情故事的配角
李碧華《青蛇》出版於1986年,改寫傳統《白蛇傳》文本,以青蛇的角度論述。青蛇與白蛇一同成長,道行五百年低於白蛇,以半丫鬟半妹妹的形態共同沾染紅塵。小青比白素貞懵懂,如同少女,本不識於人間情愛,倒與素貞的姐妹情誼裡有點同性戀的影子;但見素貞千方百計都要擄獲許仙,她在旁邊寂寞妒嫉,又想品嚐凡世情欲,於是起了勾引許仙之念。如此構成三角,又遇收妖的法海和尚介入。小青以一種不受拘束的好勝之欲,在危急之際誘惑法海,亂了他的定力,起了生理反應的法海老羞成怒要收小青——原來他想要的是許仙。小青則是大感女人的尊嚴受創,且憤怒於男性的虛偽。最後水淹金山,白蛇產子,四口六面,法海用雷峰塔壓了白蛇,小青則手起劍落了結軟弱的許仙。幾百年來,小青就在西湖,一邊等白蛇出世,一邊寫她自己的愛情故事。
這真是一個少女的成長故事,李碧華開出來的情愛與欲望之層次與型態,遠比古老的傳說豐富。從第二女主角的角度去講,一種「總是輪不到我」的心情,小青雖落得孑然一身,但她對男人與情愛比白蛇看得更透,用妖的話來說就是道行更高,用人的話來說就是更成熟。自立自強,能夠親身清除自己的欲望對象,還懂得講自己的故事更以此賺錢,這其實已是一個現代社會女性自立的範本。配角可以旁觀者清。小青怎麼說?「我一天比一天聰明了。——這真是悲哀!」
自閉者的溫柔
獨身女子必定無情?親愛的,沒那麼簡單。西西〈像我這樣一個女子〉亦是寫於八十年代,論出版比《青蛇》還要早一點,1984年洪範出版以此點題的短篇小說集。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位死人化粧師,戀上了一位青年夏,夏要來看她工作的地方,「我」在咖啡廳中等他,心裡充滿了矛盾掙扎,怕夏像以前的男人一樣,被她的工作嚇到調頭就跑。故事通篇以第一人稱內心獨白體寫成,迴環往復的重複著「像我這樣一個女子,原是不適合與任何人戀愛的。」這句話,不但獨身女子的座右銘,大概也曾浮蕩在任何受困於情的女子心中。在愛情面前,人人都千瘡百孔,自卑自憐,覺得無可托信,鞭長莫及。
〈像〉簡單好讀,大學時曾作為中文系導修課文本。課上男女同學口徑一致,竟覺得女主角十分可怕,怪不得沒有人愛,「換著我都不會愛她」。我才驚覺,原來在現實社會,女性坦露自己的心情,就已經叫人卻步了。但這女主角思慮過多,卻也反省到很深的地步,她突然怪責自己不應試煉愛人:因為愛與勇氣,本可以是不相干的兩回事。這難道不是體諒對方、自我反省的溫柔?一個人如果能真的認真思考自己與戀人的關係,體會對方的心情,就算是憂愁封閉,也可以是溫柔的。
我在課上幾乎是氣急敗壞地指出這點,同學都靜了,呆呆的望著我。所以,獨身女子,看來是很難讓他人認同的了。「像我這樣一個女子,原是不適合與任何人戀愛的。」始終是文藝女生共同的自許,孤標傲世偕誰隱,如果經濟能力等等狀況允許,生活好好的,實在未必要去受此一遭磨難。
禮物的邏輯
獨身女子是一個經濟問題,但它又始終不只是經濟問題。這個城巿已經太常以經濟去考慮事情。謝曉虹的短篇小說集《好黑》裡有一篇〈葉子和刀的愛情〉,暴烈的魔幻寫實手法,描寫了困在庸俗愛情考慮中的一對戀人:葉子和刀。他們住在一起,生活裡充滿了愛情的表示,比如煮飯給對方吃、送各種禮物給對方——大量的禮物,要排隊輪候,花金錢時間心力取得,這些壯舉代表了付出,代表了愛情,已經蓋過愛情本身。葉子和刀已經失去超越物質和習俗來互相關懷對方的能力,無法對應對方的情緒而行動,也無法在對方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安慰。
資本主義的獲取與付出,定義了我們的愛情,這裡面還有一種競勝心理,即我要付出得比你多,讓你心存虧欠。當其中一方受傷,葉子和刀都只能透過傷害自己來作為反應,終於各自把自己的一條手臂砍下來了。小說在荒誕的高潮上一頓,魔幻寫實成為愛情的救贖:二人各自提著對方的斷臂上街去醫院,終於以對方的斷臂去撫摸對方的後臂,得到一點葉子記得的「愛情最初的感覺」。
 這個小說兼揉冷酷與甜蜜,切中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愛情困境。而小說透過肢體的分離,自身的殘缺,才能達到一種些微的溫柔接觸。愛戀中的人,原也可以是極度自我中心的;那末,獨身女子的狀況,也就反而如同與一切進行戀愛,她隨時可以把自己變成一件禮物。匱乏與完整,原也是一個銀幣的兩面,這或者是愛情最牢不可破的核心。
這個小說兼揉冷酷與甜蜜,切中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愛情困境。而小說透過肢體的分離,自身的殘缺,才能達到一種些微的溫柔接觸。愛戀中的人,原也可以是極度自我中心的;那末,獨身女子的狀況,也就反而如同與一切進行戀愛,她隨時可以把自己變成一件禮物。匱乏與完整,原也是一個銀幣的兩面,這或者是愛情最牢不可破的核心。
刊《號外》十一月書評別冊